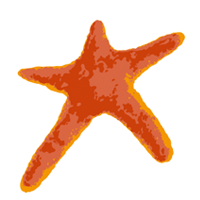荆棘之路:“救命药”诞生的这三十年
2014年,恒瑞医药的抗癌药阿帕替尼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晚期胃癌的治疗。业内人士和投资者没人看好:相比瑞士罗氏制药(Roche)生产的贝伐珠单抗,阿帕替尼副作用大,加上舆论普遍觉得“国产药不行”,二级市场反应寥寥。
但对于大量经化疗无效的胃癌晚期患者来说,阿帕替尼却是天降救星:国外原研药吃不起,去印度买药又麻烦。罗氏的贝伐珠单抗一个月要吃掉5万块,阿帕替尼只要2万,成了许多患者的唯一选择。
紧接着,恒瑞医药通过医保谈判,顺利让阿帕替尼进入医保报销目录,2018年阿帕替尼的销售额超过了20亿元,一时风头无两。
阿帕替尼揭开的是中国医药行业一道隐蔽的伤痕:当资本市场为行业的繁荣欢欣鼓舞时,很多重疾患者还在高价进口药的阴霾中艰难求生,蒸蒸日上的国内药厂,在很长时间里都做不出本国人民的救命药。
2004年,恒瑞开始启动阿帕替尼的临床研究,彼时国内医药行业,还沉浸跃进热潮之中,时任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狂发批文,众多刚成立的医药公司,到处寻找老祖宗们留下来的药方,来制成各种中药丸剂火速上市。直到三年后,郑筱萸因受贿被判死刑,狂热才偃旗息鼓。
比起老祖宗秘方借壳上市,做仿制药甚至创新药周期长、成本高,成功率飘忽不定,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上溯到90年代初,中国医药还没有创新和仿制一说,除了大城市有着改革开放后外资药企新带来的药品,国内大部分城市的药店名字里,都还带着一个饱含传统特色的 “堂”字。
1992年,刚刚晋升连云港制药厂厂长的孙飘扬连凑带借花120万,购买了抗癌药异环磷酰胺的专利权,当时药厂一年的利润还不到100万。就是这款同样作为工艺改进的新款抗癌药,让药厂第二年的销售额便突破一亿。
尝到了甜头的孙飘扬又找到自己在中国药科大学校友,合作开发了在外企原研药基础上改良版的胃癌化疗药品伊立替康,打破了抗癌药国外垄断的局面,并于1998年成功上市。2003年,连云港制药厂更名为恒瑞医药,这款药至今仍是恒瑞的现金流产品之一。
从赚到第一桶金,到规模化生产市场主流产品,再依托产品线和业务布局转型高投入、高收益的创新研发,是包含辉瑞、强生、诺华等几乎所有跨国药企巨头都走过的一条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通过引进外资药企,寄希望用市场换技术,让国内医药企业能复制这条“原始积累—仿创结合—全面创新”的发展道路。但因为种种原因,国内的药企还是“走了一些弯路”,也在今天深刻影响着千千万万中国患者的健康与命运。
01. 四大家族:中国医药的原始积累史
在恒瑞赚到第一桶金之前,国内医药产业刚刚完成最原始的工业积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医药的原始积累,基本可以归结为一部 “四大家族”变迁史。
最早的医药“四大家族”可追溯到民国时代:民生、信谊、新亚、海普,这四家活跃药企都诞生于1920年前后的上海,并称为“民国四大西药厂”,因其历史悠久,一度被称中国制药工业的元老,直到如今仍可以找到其痕迹。
最为着名的是1916德国药学博士霞飞在上海创立的信谊大药房,其生产的抗菌药“消治龙”软膏,作为战略物资广泛用于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时期曾一度成为囤积居奇之物,不少人甚至用黄金购买该药以作投资之用。
但这仅有的几家大的药厂,当时只能在上海这种稍有工业基础的地区发展,随之而来的战乱,让这些药厂拆的拆、迁的迁。因为缺少技术和资源,这段时期国内医药工业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专门掌管共和国卫生事业的部门随之诞生,自此医药工业发展被提上了日程。其中华北制药、太原药厂、新华药厂和东北制药四家药企,因为享受到工业重镇带来的政策和地理优势,并且在前苏联的扶植下规模迅速扩大,便成为了建国时期的医药“四大家族”。
这些成长起来的规模化的药厂,一度改变了国内用土霉素、红药水、紫药水“三大神药包治百病”的窘状。但这些药企始终都没能脱离“化工厂”属性,生产出来的原料药和橡胶、水泥、螺丝等工业品没有本质区别,是整个产业链上利润低下的一小环。
改革开放后,先后有四家跨国药企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分别是:西安杨森(1985年)、中美上海施贵宝(1985年)、华瑞制药(1987年)和中美天津史克(1987年)。这四家药企的产品在国内上市后,很快便占据了各大医院的药房,基本取代了原来四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行业地位。
“新四大家族”除了极大丰富了中国药品市场之外,另外一个贡献是把“医药代表”这一职业带到了中国,有了基于循证医学的营销体系,国内很多所谓的“药品”才逐渐具备医疗服务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土制药企业从原料药向品牌药方向转变,仿制药和创新药的概念随之诞生。
几种药品的类别
就在四大家族改头换面的同时,江苏东北部一座临海小城连云港,为了顺应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浪潮,也设立了四家药企,分别是康缘药业(连云港中药厂)、豪森药业、正大天晴(连云港东风药厂)以及恒瑞医药(连云港制药厂),考虑到这四家药企在顶峰时的市值加起来超过7000亿,姑且可称为“连云港四大家族”。
其中,正大天晴崛起于肝病用药,康缘主打中药,豪森发迹于精神类药物,恒瑞则主打肿瘤药。在外资药企还未大举涉足肿瘤用药领域的时候,恒瑞率先通过异环磷酰胺和伊立替康等产品占据了该领域。尝到了做创新药利润高、竞争小的好处,孙飘扬斥资两亿在上海建立新药研发中心。
但与高利润对应,药物研究几乎是全球商业领域中效率最低的,全球96%的药物研究项目都以失败告终[1]。不过,孙飘扬选了条曲线救国路:将药物进行1.5次开发,通过改造修饰已有的新药做成仿制药,同样属于创新,市场也不小。
有伊立替康的成功经验,加上花重金投产的研发设施,恰逢外企上市的一系列新款肿瘤药品,在国内专利系统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下子让孙飘扬的实验室有了用武之地。
于是,孙飘扬开启了自己仿创结合之路。如果按照海外的成功经验,完成了原始积累阶段的中国医药行业,应该利用国内“技术换市场”的窗口期,开始投入研发,走向仿创结合。但后面的事实证明,这条路并不好走。
02. 行业跃进:政策和专利的超级红利
80年代末有一句口号在广大内地流行:“要当好县长,先办好药厂。”
这句口号反映了一个事实:整个华夏大地仍处于一个缺医少药的状态。仅有的几家合资药企并不能满足13亿人的用药需求,除了少有的几座城市,内地广大群众吃的还是用牛皮纸包的中草药。
面对一片蓝海,企业需要将药品从工厂里推销到医生和患者手中。于是在国内经济刚刚更名换姓后,广大企业家瞧准了带着“民生”属性的药品市场,在全国各地兴起了各种医药流通企业。
其中,作为国内第二大青霉素生产基地的哈药集团,成立销售公司打起了“蓝瓶钙”的广告;发明了药气针的步长制药,也趁着处方药广告禁令未至,学习哈药砸下1200万买下了12个卫视的头条;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华北制药第一次拿下了中国驰名商标。
从1996年到1998年两年内,虽然医药系统经历了各种反腐风暴,超过4000项回扣案件被立案调查,372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少医院都因此垮掉[2]。但这似乎并未阻挡中国医药工业跃进的脚步。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医药监管合并原卫生部的药政司,吸收国家中药管理局的部分职能,组成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DA),结束了此前长达16年药管局、卫生部以及地方卫生厅“九龙治水”的情况,监管、审批效率得到空前提升。郑筱萸出任第一届SDA局长。
第二年,国家经贸委为了迎接入世后药品市场来自国外的冲击,发文指出“要用5年时间扶持10个有竞争力的特大型医药流通集团”。
庙堂的本意,是以海外冲击来倒逼国内药企走华为路线,通过自主研发对抗海外竞争。结果很多药企只看见了药品监管的放水,选择了某家电脑组装公司的路线,国内医药行业活跃程度自此达到了顶峰。
2003年10月,在成都举办的第50届全国药品交易博览会上,标准展位超过1400个,特级展位面积加起来能装下两个足球场,展位的预定需要托关系找熟人,不少企业需要2到3家合用一个展位,参会人数更是史无前例地超过10万人。
政策“利好”下,不少后来成为“百亿品种”的药品也在此期间获批。其中石药的第一大销量单品恩必普,开启了一个药拉动一个公司的神话;天士力的抗肿瘤产品蒂清,摆脱了“纯中药公司“的称谓。罗氏制药另一款用于治疗乳腺癌的生物药曲妥珠单抗,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考虑到生物制品的临床复杂性,以及当时国内监管机构对其认知程度,生物药上市审批效率并不高。曲妥珠单抗2002年9月份申报,第二年5月份就获批,速度堪比如今的FDA(美国药监局),国内肿瘤患者能够快速用上全球最新的乳腺癌特效药。不得不说郑筱萸时代下的药品审批,还是有那么些正向作用。
而嗅到了热闹气息的孙飘扬也没有闲着,先后与上海医科院、北京医工所、天津药研所等机构开启合作。几年内成功上市了市场上主流的肿瘤产品:奥沙利铂、多西他赛、替吉奥、卡培他滨……这些直到现在都还广泛使用的化疗产品,为恒瑞带来了充足的现金流,恒瑞的销售额很快迈入20亿大关。
到了2006年,恒瑞毫无悬念的成为了国内肿瘤市场市场份额最大的玩家,之后其仿制药之路继续扩张,药品领域也从原来的肿瘤、麻醉、造影剂,开始逐渐向心血管、糖尿病等临床常用药领域延伸。
纵观本土医药这段发展历史,在专利法和政策窗口期的双重红利下完成了规模上质的提升,却没能借助规模效应去覆盖药品研发的周期风险完成转型,其中的恶果,也会在未来几年逐渐显现。
03. 历史弯路:仿制药质量问题的源头
2004年在某场行业论坛上,一位外商问到中国的医药企业家:“联合国每年采购60亿美元的药品援助非洲等贫困市场,欧美、日本,甚至连印度都会去参与竞标,你们是抗生素生产大国,为什么没有公司去呢?”
后者很无奈地回答一句:“我们的抗生素过不了FDA的认证。”
在跃进时期,《药品管理法》做过一次修订,规范了仿制药的审批程序,但最令人咋舌的的一点是,该办法允许“在无法获得原研药时,可选用已上市的国产仿制药作为参照物”。“一仿”本就不靠谱,接下来的“二仿”、“三仿”、“四仿”……“越仿越不像”,药效可想而知。
食药监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处长李正奇曾毫不留情地撰文称:“国产仿制药总体质量比原研药相差远,有的甚至是安全的无效药。”
2004年药监局批下的新药批号为10009个,同期美国的这个数字是148种。审批宽松下另一恶果是让大量玩家得以迅速入场,截至2016年,中国有超过4000家制药企业,近1.3万家医药批发企业和超过40万家零售药店[6],多数是跃进时期的产物。
玩家增多便将药品利润摊得像纸一样薄,药企更遑论注重产品质量。对此有地方食药监系统的专家一针见血道:“要求20分可以及格,企业做到21分就可以,做多了就觉得是浪费。”
但回扣盛行下的药价并没有降下去,在一个批文对应一个药品的年代,许多药厂将“降价死”的产品,添加一些淀粉等辅料,改头换面又成为“新药”,继续高价进入医院赚钱。
而在药物采购端,原本是应该是价廉质优的药品对患者更有利,但在2015年前实行的是国家招标、医保买单的政策,药物的使用者并没多少发言权。招标的导向是拼命压药价,而得益于地方保护主义,每次药企都能找到方式生存下来。
2005年,湘雅二医院的药房进了一款从鲜芦笋中提取的药物芦笋片,用于“缓解化疗后口干舌燥、食欲不振”。该药品出厂价为15.5元,医院最终零售价为213元一盒,高达1300%的利润竟不存在任何违法的操作。经媒体曝光后,才查清是因为当地药品招标采购管理部门将其市场指导价格定为136元。
2010年山东37家医药企业联名上书省卫生厅,反对枣庄市服务业办公室将市内几大公立医院的药品配送权全权授予山东海王药业,一时引起轰动,最终联名盖章的企业达到了98家[3]。
山东海王这家连产品都没有的医药企业,仅靠几个城市里的药品周(yun)转(shu)业务,2009年的销售额有41亿元,足以让顺丰和三通一达汗颜。
这两件被曝出来的极端案例,反映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在仿制药大肆横行的情况下,本土药企的核心竞争力成了政府事务能力——你能否在招标以及准入中进行议价。跟企业是做新药还是仿制药,甚至有没有药都毫无关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每年国内制药企业稳居A股销售费用占比排行榜第一名,而长时间以来国内药企创新投入比只有1%,研发费用加起来不及全球TOP10当中的任何一家。
恒瑞主打的抗肿瘤以及麻醉等领域,虽然有较高技术门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后续仿制药的攻势,但随着时间推移这道护城河也逐渐被攻破。
而此时国内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疾病的用药,离不开外企的产品。尽管有热心的行业人士呼吁到:“如果13亿国人的健康需要依靠国外企业来保障的话,那有可能关系着这个民族的存亡,” 但也无法扭转大部分药厂90%都是销售人员这一现象。
平心而论,当局虽然在引进外资入华时给到了税收、单独定价等政策优惠,其给到本土医药行业的支持也并不少:从审批流程快,到适应症范围比原研药多,从生产标准到销售合规性,监管一直给到较宽松的标准。
2000年中国加入WTO,药品专利权和全球对接,中国没办法像印度制药行业那样厚脸皮地在专利保护期内进行“强行仿制”,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内药企在大部分的原研药企专利诉讼官司上都没吃过大亏,在进口药专利期结束前就上市的药品更是数不胜数。
2005年前后监管放宽带给行业的揠苗助长,起到了一定的鼓励性,使得国内药品品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丰富,但07年新版药品注册管理法以及后续药改政策并没起到大浪淘沙的作用,反倒是把本土的医药工业带到了一个“上有政策,下出对策”的循环中。
04. 创新窘境:医药研发的至暗时刻
一个四川企业家在评价中国医药行业的创新时曾说,“三分之一的企业自强不息,三分之一的企业奄奄一息,三分之一的企业无声无息。”
90年代,步长制药全国卫视打广告时,孙飘扬花了2个亿在上海盖研发中心。但对于新药研发,原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陶剑虹这么描述道:“这就相当于花大把钱雇佣数千名艺术系的学生,对其工作进行数十年的资助,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有人画出一幅蒙娜丽莎。”
这句话很形象地阐述了新药研发的两个前提:巨量资金+研发人才。和如今一个免疫治疗药品有127家创新药企和背后的投资机构扎堆不同,在资本游戏还不流行的年代,国内的新药项目要找投资方,简直比登天还难。
早在“千人计划”回国潮开始前,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就抱着一款新药分子回国,立志要做“中国人吃得起的新药”,但是因为财务报表不好看,找了一圈都没投资人理,这款被后来的卫生部长陈竺誉为“堪比民生领域‘两弹一星’的重大突破”项目差点胎死腹中,最后还是靠杭州是政府的1500万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恒瑞医药依靠仿制药业务和2003年的上市,资金倒是很充足。人才问题上,孙飘扬找到了自己的校友。2009年,在布局糖尿病产品线时,先挖来了药大硕士、美国礼来首席科学家郑玉群,随后挖来了82级的同学、礼来的高级化学家张连山,张连山和郑玉群,又向恒瑞医药引荐了礼来的资深研究顾问曹国庆。
这一波操作,让恒瑞医药加快了自己在糖尿病领域的研发进程,和近期医保灵魂砍价药物达格列净同一机理的恒格列净,马上被提上了研发日程,恒瑞也借这波势头,进一步扩张了海外业务。但面对恒瑞的挖墙脚,礼来终于坐不住了。
2013年的国庆节刚过去,美国礼来制药指控前雇员曹国庆涉嫌向中国恒瑞医药泄露价值5500万美元的商业机密,并声称已经掌握其拷贝的相关资料和邮件等关键证据。消息传到国内,一经发酵,恒瑞两天便大跌6个点。
这份指控很讲究:首先这是美国联邦法院,而非一般的州法院接待;其次,恒瑞如果站出来以公司名义为两位员工辩护,则将陷入以公司为主体的诉讼案中,企业自身形象也将严重受影响,而如果放任不管,恒瑞在对待员工上同样会受到舆论攻击,其人才战略将受到影响。外资药企这次是“有备而来”。
但随着恒瑞的主动出击和美方的证据不足,再加上来自国内官方的“支持”,胜利的天平很快倒向恒瑞这一方,礼来不久后便选择撤诉。除了一些专利诉讼称得上“阻挠”,国内药企的创新药进程并没有受到更多来自外部力量的堵截,创新遇到的更多的问题还是在内部。
制药行业流传这样一句话:“谁搞创新药,谁就是在找死!”这句话并不是为了出风头,恒瑞布局研发后的第一个创新产品从立项到上市,足足花了10年时间。国内做新药的企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审批慢。
2007年郑筱萸被执行死刑,药品审批迅速按下了刹车键。新版药品注册法问世,规定了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详细审批过程,但由于审批本身缺乏经验、没有标准,再者郑筱萸作为少有被处以极刑省部级官员[4],后来上任的药监领导,无不忌讳审批的风险性。二者叠加下的国内药品上市审批从此步入慢车道。
前美国药监局(FDA)局长Scott Gottlieb曾就美国药品审批缓慢提出过一个加速办法,他提出要用“无缝试验”区管理新药临床审批,组织大量的开发人员和肿瘤医生,将临床试验和审批同步进行,在这样的模式下,美国最快28天批了一个药。[5]
虽然这种“美国速度”是靠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烧出来的,国内药企没办法复制,但国内药品审批速度着实慢。国内新药审批没有28天,也没有28周。2014年,这个时间是42个月,而晚期肺癌患者的平均生存周期才14个月,广大肿瘤患者只能去海外购买救命药。
每一个创新药的背后,都是巨量研发资金投入,晚上市一年,便意味着晚一年的回报。而一款药历经几十个月获批上市后,并不意味着能马上产生利润。创新药要进入医院,需要通过省级招标,彼时国内各省招标采购周期不统一,错过招标时间便需要等待新一轮招采,短则一两年,长的话需要等5年以上。
此外,药品的使用权在医生手里,后者会参考自己的用药经验,在临床上更加偏好常年打交道的仿制药,整个社会对于新药的认同度不高。再加上高定价和有限的医保资金又互相冲突,反倒是广泛被接受的仿制药,更能得到医保的青睐,每年占据着大部分的医保资金支出。这一来一去,新药上市后很难及时用到患者手里。
我国第一个国产创新肿瘤靶向药,前文提到贝达药业的肺癌药凯美钠,是靠着浙江省委书记的特批才得以于2011年加速上市,但上市7年多,全国仍然有90%的医院开不出这款药。
环境的不支持加上回报不明确,创新药的投资积极性自然深受打击,国内的资金纷纷流向拥有“保护品种、独家工艺”的中药企业,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云南白药花式做牙膏,片仔癀高调进军美妆领域,白云山把凉茶广告打到了央视……有了资本的支持,中药企业纷纷玩起跨界。
但回到本章开头,新药研发本身和芯片类似是一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且周期漫长的过程,本就环境不好,又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中国创新药陷入负向循环。
2014年一位民营医药企业家在接受中国经济网采访的时候说道:“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过去60年属于自己原创新药只有三个半。”一句话就把中国的创新药发展史,概括的八九不离十。
顶层设计并没有找到一条有建设性的药品改革方向,而国内的药企自己也不够争气,只是随波而流:放弃高风险但高回报的研发,和当局的降价政策打游击,用不断刷新大众认知下限的“神药”充斥中国的医药市场。
05. 柳暗花明:创新药的春天来了吗?
201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一位姓毕的主任走马上任,在此之前,CFDA由副部级升级为正部级,似乎奠定了医药行业大变动的基调。
新领导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肃国内药品质量低劣的问题。2015年7月22日,CFDA官网上一则临床试验数据自查公告,要求参与新药申报的企业,尽快核实自己产品临床数据的有效性。
彼时的药品临床试验不规范已经成为常态,试验数据情况不乐观,一般联系第三方机构重新处理一下,便可安然通过审批。因此,对于这则公告,众多产品待审批的药企,都抱以观望的态度。但接下来,官网上不断刷新的检查报告,让广大药企意识到:这次审查标准,是玩真的。
此次临床自查活动,一共涉及1429项受理,最终企业主动撤回和强制退回的有1233项。这一年,86%申请上市的新药,在新标准下都不合格的!
此外,CFDA将提了好几年但一直没有落实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政策重新提上日程。彼时全国有超过4000家药企,[6]近19万个药品批号,每个批号的背后都是一家药企的投入,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触动利益如同触动灵魂。
但CFDA决心似乎很强烈:2016-2017年,仅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配套文件,就一共发布了25个。对此一位从业长达20年的医药投资人评论道:过去是伸着脖子等政策,现在是政策多到连团队都分析不过来。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要求仿制药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生物等效(BE)实验,一项BE实验花费基本相当于很多仿制药企一年的销售额。BE试验需要相应的研发资源,讽刺的是全国4700家药企中,九成的中小型药企根本没有研发中心。
为了鼓励药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CFDA将该政策和药品招标采购相结合,规定公里医院的药品采购,要从完成再评价工作的产品中遴选。齐鲁制药用于治疗肺癌产品吉非替尼片,完成一致性评价后,在2018年带量采购过程中因为降价幅度大,顺利纳入全国11个重点城市医院的唯一采购目录中。
本次药改,先用一致性评价淘汰掉部分落后产能,将各大药企产品质量拉到同一起跑线,再启动带量采购等招标政策,让场内玩家真正回归市场化竞争,质优价廉者脱颖而出。
此外,2017年10月,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办公室共同颁布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这份文件为创新药审批提供了快速通道,被圈内人评价为“百年一遇的好政策”。
恒瑞医药用于肿瘤辅助治疗的新药19K,在临床自查撤回申请后后,于2017年3月24日重新申报,仅用了一年时间便获批上市,同样还有正大天晴的肺癌产品安罗替尼,从申报到上市只花了409天。
CFDA对进口药也一视同仁,阿斯利康药业一款肺癌药奥西替尼,上市审批仅仅用了7个月,这个速度在全球都能排到前列。
更重要的是,国家医保机构在新药上市后很快便开启谈判准入工作,虽然进入目录有一定的价格降幅,但基本改变了药企有药但患者还要跑到印度去买低价仿制药的情况,同时让新药上市后研发企业能最快的收到回报。
支持充分,竞争公平,回报丰厚,CFDA一下子激活了中国创新药体系。做创新药等于找死,不做是等死,这个结自此解开了。
2015年,恒瑞将一款创新药PD-1(SHR-1210)以7.95亿美金转让给美国一家公司,后者可以拥有其海外的临床开发及销售权益,预示着其创新布局进入收获期。阿帕替尼上市后,顺利为恒瑞带来充足的先进流,除此之外,乳腺癌用药吡咯替尼、紧跟时代的免疫治疗产品PD-1纷纷获批上市。
2019年10月,孙飘扬在一场行业论坛上喊出了“砍掉恒瑞70%的仿制药业务”的口号,高调宣布恒瑞将转型创新药企。孙飘扬也因为恒瑞市值再创新高,登上胡润排行榜,走入大众的视野。
纵观国内创新药行业,海归博士杜莹创立的再鼎生物成立三年就年在美国上市;俞德超创立的信达一年内两次与美国礼来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本土创新药项目也第一次转让给全球TOP10药企……
近30年的曲折跌宕之后,中国医药行业总算勉强踏进了“全面创新”这道门槛。
06. 尾声
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出台前夕,因为医药产业没能进入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名单中去,对此天士力董事长质问到:“下一个三十年,中国人的吃药、健康问题谁来保障?”云南白药董事长则更直接:“如果13亿国人的健康需要外企来保障的话,那有可能关系着这个民族的存亡。”
12年过去了,中国患者经历过去海外购药的辛酸,经历过面对高价原研药的无助,国内医药行业终于从疮痍中逐渐走出,而在即将迎来严峻老龄化挑战之时,12年前的问题,如今看来依然尖锐,12年前的警告,如今听来依然刺耳。
一个伟大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用绚丽的数据和叙事来佐证,但具体到老百姓最基本的吃药和健康问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艰苦推进。鼓励创新,永远都不会晚。
参考材料:
[1]《主流——中国药企领袖智慧》,陶剑虹、谭勇,2005
[2]《中国药改往事》,王晨,八点健闻,2019
[3]《98家医药商业企业联名上书质疑山东海王》,孙秀红,新浪财经,2010
[4]《重磅!中国医药:改革出牛市》,君临投资汇,2018
[5]《谁能成为中国的“华为制药”》,李进,2019
[6]《变革者毕井泉》,梁振,医药界,2018
来源:财经戴老板 作者: 安格斯